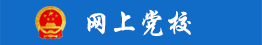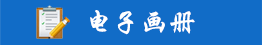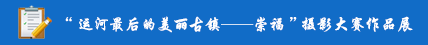横街故事,邀你一起聆听

横街老房子。(照片由崇福镇镇政府提供)

夏日里静谧的巷弄。
中心记者孙溟苑/摄

100多年前的某一天,在横街的东端浒弄口,也就是靠近大运河那头,一位硝皮师傅用煮熟的皂荚籽水硝皮脱脂后,将用剩的皂荚籽倒在了弄口垃圾堆上。不想这煮熟的皂荚籽里面竟有一粒“漏网之鱼”,氤氲着大运河的灵气,这颗“福大命大”的皂荚籽生根发芽,慢慢长成了一棵郁郁葱葱的大树。百年来,这棵皂荚树守护着横街。
横街东西向,东横街在清末民初,商家鳞次栉比,是崇福镇的商业中心。而被称作“登仙坊”的西横街,则是名人汇聚的地方。
老街从来不缺古韵故事,在它冗长的历史岁月中,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就像星星散落银河一样,撒在街头巷尾。
一砖一瓦,皆是沧桑
早上9点不到,日头已经把横街上的黑瓦片晒得“油光发亮”,略显狭窄的石板路上落满了细碎的阳光。几个手摇蒲扇的阿姨,怕日头太晒,挨着南墙慢慢走着。
沿着横街一路从西往东,两旁白墙墨瓦,老房子砖红色窗棂和木门油漆斑驳,偶尔从房间里传出来几段越剧声,让空旷的老街的显得格外寂静。
知道记者来访,今年91岁的朱解良特意给门留了一道缝。一楼大约5平方米大小,中间摆放着一张红褐色的八仙桌,桌上放着一台小小的电视机,刚刚的越剧声便是从这里传出来的。
朱解良家旁边有一条长长的巷弄。夏天太阳热烈,老房子是砖木结构的,白天时二楼烫得都没法住人。为此,朱解良特意买了个简易床放在一楼靠近门口的那一侧,作为夏天临时的卧房。这样一来,不大的房间显得更加拥挤了。
朱解良出生于上海,曾经是一名牙医。1970年,由于原先房子拆迁,朱解良带着一家人搬到了横街,住在一幢一个门面两层高的房子里。后来因为工作的原因,他又搬去洲泉。横街的房子便空了出来,直到他退休,房子才开始重新住人。
砖木结构的房子,经历风吹雨打,墙体已经开始斑驳脱落,木头做的窗子年久失修,与墙体有微微的脱离。为了看上去更“美观”些,朱解良曾买了一些白色的硬板纸准备把斑驳的墙面重新“修容”一下,无奈年纪太大了,拿钉子订了几处便放弃了。
朱解良早上起得比较晚,所以不赶早上的茶市,却极喜爱下午去茶馆。每天吃好中饭,他就拄着拐杖上街去,到下午3点再赶回家烧晚饭。朱解良说,他刚在横街住下的时候,虽然店铺已经不多了,但是人很多,每天从早闹到晚,各种嬉笑声不断,而现在周围却很少有能说说话的人。“隔壁没有人了,再隔壁也只有一个老人,平时面都见不了。”他的语气中透着一丝无奈。这可能就是朱解良爱去茶馆的原因,因为那里热闹。
一东一西,满是故事
横街有东西横街之分。西横街,旧称“登仙坊”,听名字就知道,这是一块风水宝地。明末清初名士吕留良出生于此。现在这里还保存着不少名人故居,如明代布政使劳永嘉,清初浙派诗人代表人物吴之振的守愚堂,清后期著名画家吴滔的故居,民国沪军都督陈英士学过生意的善长当,秋瑾挚友徐自华的故居,足球名将戴麟经的戴家楼故居,我国著名桥梁专家、中科院院士程庆国的故居等等。
走在幽深的弄堂里,就好像行走在历史中。
沿着横街从西往东走,就会发现,越往东,人越多,越热闹。这与西横街相比,又是另外一种感觉。
在靠近大运河的那一段,这里还可以见到一间修葺一新的小平房,门外堆满花花草草,乍看还以为是一间小民宿。“小民宿”对面,便是姜顺福的家。虽然没有像对面的房子弄得那般“精致”,但白色墙面毫无斑驳的痕迹,也看得出是花了心思的。
今年71岁的姜顺福是土生土长的崇福人,自小便住在横街。在他的印象中,东横街上做生意的人比较多,“很多绍兴人在这里做皮毛,还有木匠店、打铁店……”而西横街上,则多是茶馆、糕团店、米店等。
每天五六点,老街上就已经很闹猛了。前来赶集的人们会占满街道的两侧,小贩的阵阵吆喝声此起彼伏。有些调皮的孩子,还会跟在沿街售卖的小贩身后,有模有样地学着,直到被父亲拎着耳朵扛走。
夏日傍晚的横街,盛况可一点不比早市差。四五点的光景,家家户户就已经在门口放好乘凉的板凳。这凳子可不是随意放的,它可是门大学问。你得先学会判断那晚的风从哪里来,以便最大程度感受凉爽。于是,那时的傍晚,总会有一群小孩子拿着椅子奔来奔去,好不忙乎。
在姜顺福的叙述中,记者仿佛也重回了多年前热闹而充满市井气息的横街。
到了夜晚,这里又恢复幽静。偶尔从巷弄里传来几声狗叫,但没一会儿就安静下来了。若这时有人从横街走过,踢踏踢踏的声音撞在青石板路上,显得分外清晰。
后来,青石板路铺上了厚厚的水泥,这里的店铺渐渐往北边的崇德路迁移,年轻人开始走出横街,去往更“宽阔”的地方伸展手脚。但老街的夜晚依旧是幽深宁静的,这里住着的大多都是老年人,早睡早起,不舍得离开住习惯了的老房子。
就像这条老街一样,静守岁月,随遇而安。